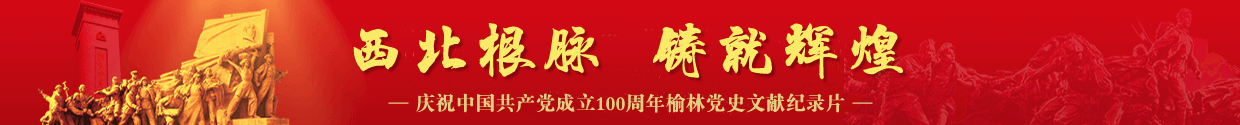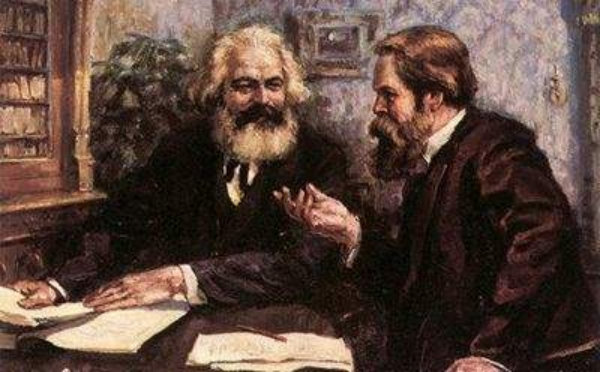广播电视的市场化应当是服务的市场化
人物简介:霍宝林,生于1965年,清涧人。现任米脂县广播电台副台长,一级播音员。1985年参加工作,曾任榆林县广播站、陕西省广播电台、宝鸡市广播电台、米脂县广播电台播音员、主持人。从事广播电视工作33年,曾制作联合国2744项目验收专题片,《闯王桑梓行》、米脂窑洞古城一条街评审专题片以及《李自成传说》《铁水打花》等米脂县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专题片20多部。1985年获榆林地区优秀播音一等奖,1989年获宝鸡市优秀播音二等奖,2005年获陕西省优秀播音三等奖,2009年获陕西省优秀播音二等奖。2016年创作的广播剧《沙家店战役中的米脂婆姨》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优秀广播剧二等奖、榆林市优秀广播剧一等奖。
每根路灯杆上都有广播喇叭
我进入广播行业是在1985年。85年的5月份到榆林考试,7月份接的通知,8月份上的班。
80年代,全国县级广播电台都是以有线传输为主。无线广播,中央台、省台和省级市台有。地级市台就没有了。比如榆林,就是拉一根铁丝线,广播线,有线传输。那会儿在榆林地区,米脂县的有线广播是搞得最好的,为什么呢,其他地方都是用木杆撑起铁丝,往往几年就朽了、倒了。米脂县是最早实现全县村村通水泥杆。所以它那个广播传输质量是非常好的。70年代到80年代,全榆林地区、全陕西省,甚至全国都向米脂学习过。到90年代,有线广播就被调频广播取代了。
那时候榆林全城,大街、二街、三街都有喇叭,每一根路灯杆都有一个广播喇叭。我记得报到第一天下午,就让我试播天气预报。当我把那个天气预报录音带往上一放,键钮一按开始播天气预报的时候,满大街所有喇叭都在响,那个声音效果特别好,我的声音传遍了全城,我当时那个自豪感啊……
县级广播站五几年就有了,一直有播音员。米脂广播电台也是五三、五四年就有了。但到80年代,人们对播音员的普通话要求也高了,对老播音员就不太满意了,所以它(榆林县广播电台)就向全地区招最好的播音员。当时一共招了4个,一个我,一个吕宏伟从靖边调的,还有横山调的许文丽,澄城县调的任小娜。后来我离开以后,他们三个还都在榆林。现在他们几个都退了,只有我还在职。因为当时我最小,刚20岁。
那时的广播非常神圣
榆林县广播站只有一套节目,每天播三次。我们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钟楼,机房也在那儿。编辑室在钟楼巷下面。播出都在钟楼上,比较安全。那会儿的广播,非常的神圣,管理比现在要严的多,门经常是锁着的。一般人钟楼上不让上来。像省台的话,是武警守卫。广播就怕有敌特分子搞破坏,宣传一些其他东西。
那时的广播节目以新闻为主。那会儿的新闻,不像现在围着会议转。记者采访,是以一种什么形式呢?每个乡镇有放大站,因为广播信号从县里送到乡镇,它就减弱了,要经过放大站放大后,再送到村里。每个放大站的值机人员就是记者,而且放大站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广播向全乡发布信息。每个乡镇,都有通讯员;每个村,也有通讯员。村里发生什么事情,马上就通知到放大站这边;放大站再将稿子通过信件寄到县里,寄到编辑室。编辑室把稿子编好,我们播出。等于是把全县的信息都汇集起来了。那会儿我们广播站是覆盖到榆林县的各乡镇,也就是现在榆阳区。当时榆林地区广播是各县管各县,只有一次向全地区的广播,1986年春(3月12日植树节)在榆林剧院有个植树造林动员大会,是向全地区直播的。那也是我第一次直播。
最早确认自己要走播音这条道,是我上初中的时候。小学刚毕业,快上初中了,我每天就在想,以后考高中不一定能考上,我得找个事儿干。干什么?也没数。偶然有一次,听到清涧县的广播。那时候每个村、每个院子都有广播喇叭。是那种纸盒的小喇叭。所以不管什么地方,只要是广播时间,早、中、晚三次,广播一响,所有人都能听到。吃饭的时候,所有人都围在广播下面,听听新闻啊,看又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中央的转完以后转省上的,省上的转完以后播县里的。县里的就收集各乡、各村的新闻。甚至像谁家的毛驴走丢了,寻驴启示我经常播。还有寻牛启事、寻猪启事。那会儿都是不收费的,又不像现在有手机传输,怎么办呢?“现在播送《寻驴启事》,某某某村,谁谁家的驴走失了,什么颜色的缰绳,什么笼头”。很有意思,农民也爱听。今年谁家种什么收什么,政府有什么政策,公购粮交多少,还有计划生育宣传……那时农村没有电视,报纸更没有,只有广播,广播是唯一的宣传平台。就从那儿开始,我决定当播音员。一下子感觉自己找到出路了,就觉得播音员这个职业很神圣。我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,只要是我对着话筒播音的时候,我必须把口漱得净净的。从职业上来说,我认为这是一种崇拜,对话筒的一种崇拜,也是对我的听众的一种尊重。对自己来说,还有一个好处是,把口腔打开了,利索了。吃过饭、吃过东西之后,感觉粘得吐字不清楚。我带学生的时候,对他们讲,如果你在做一份职业的时候,能崇拜它,把它看成一种神圣的东西,就像跆拳道,一上台鞠一躬,下台再鞠一躬,表明这在你心里是一种神圣的东西,你有这种仪式感,肯定能做好,如果没有这种崇拜,很难做好。这也是一种职业操守。
实际上我正式练习就练了一年半。我在清涧练的,没有跟任何人学,每天自己听广播练。后来买了个录音机,我跑到绥德买的美多牌砖头录音机,那会儿清涧没有。花了90多块钱。我在工程队干活儿,抱砖、提灰,假期干了两个月,挣到的钱。还买了两盒磁带,一盒4块钱。那会儿一个月工资也就20、30块钱。后来又秤了几斤铁丝,从河对面拉了一根线,拉到我们家里头。也不知道电压匹配不匹配,阻抗匹配不匹配,反正接一个插头塞进录音机那个插口里头,就开始录,我录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6点半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,效果还不错。我就天天跟着那个30分钟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,一年半,天天如此,我都能全部背下来了。
初中毕业之后,我就没事干了。早上拿点吃的东西,天一亮就到山上去。山上练一段时间以后,下来到沟里边练,再到清涧那个大桥桥洞下面练习,因为有回音。然后再到家里头,用录音机练。家里头我妈不让我练,她认为南腔北调的,不好听。她把录音机给我砸了。从那以后我再没买过录音机,到同学家去租、借。后来卡座录音机基本每家都有,我家那台砸坏之后,我再也没买过。
我爸妈是建筑工程队的,那会儿还摆个地摊,没有社会地位。你要是在百货公司什么的,很牛啊,买东西方便,那会儿计划经济么。我为什么从小学习不好,不是我不聪明,是因为同学欺负我。老师看不起,同学欺负。家里管的又不严。本来学的还挺好的,后来一直被欺负,为了躲避同学的欺凌,就不去学校了,成绩下降了。我爸妈就认为我应该做生意,卖货,或者顶个班去建筑工程队也行。我说我就干播音。为啥?一方面是我喜欢这个职业的神圣,另一方面,我是我家唯一的男孩,传宗接代就要靠我。如果我这个职业不安稳,有个什么闪失,我们家不就断香火了?我就想找个工作,风刮不着,雨淋不着,既没什么危险,社会地位还高。

1993年在米脂台
榆林县广播电台第一批合同制员工
我在家自己录好了磁带,先到清涧考,考了第一。但成绩公布之后,一直没录取。隔了差不多两个月,1985年开春的时候,我就去清涧广播局找白局长,问我这个待业青年能不能去广播站实习一下。局长说:“播音员是党的喉舌,广播电台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地方,谁想来就来,谁想播就播?那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查,要会议研究决定,允许你上你才可以上。你觉得你播得好,榆林在招人,你到榆林去考去。”我当时想他可能是气话,半信半疑问,“真的?”他说,“真的。”我就转身走了。
回到家,我悄悄收拾了一下,拿了盒磁带,来到了榆林。正好是中午12点,一天中的第二次广播时间,榆林满大街都是广播的声音。人家那播音员播得特别好。人家播这么好,不可能要播音员。我想白局长肯定是在损我呢。我就转身想走了,不考了。走到榆林汽车站,要买票。我一想,从清涧到榆林是4块7毛钱,来回就是9块多,快10块钱了。我来一回,连广播站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我去问问他总该可以吧,这个又不是太丢人的事情。又不是偷人抢人,我去问问他。于是又来到城里,问人家,说是广播站在钟楼巷。我来到编辑室,一看好多人在排队。我问这里是不是在招人,人家说是。问我哪的,我说清涧的。问你要考试吗?我没敢说自己考,说是我的一个同学要考。我对语音比较敏感,到榆林后讲了一口榆林话。我说,“我一个同学委托我上来问一下。这儿有一盒儿磁带,如果你们感觉行,我回去让他准备下,如果不行就拉倒。”他拿过磁带放到那个三洋的卡座机里。声音一出来,所有人都静悄悄地。工作人员问:“啊,这个人哪的?”我说“清涧的,我同学。”
“哎,我觉得这嗓音好像是你的呀!”
“不是,这不是我,我播不了这么好。我一个同学,人家天天在家里练。”
“这个不错,你让他回家好好准备一下。完了留个地址,我给他来信。好好准备。”
回去大概一个月以后,家里来信了。一般榆林到清涧来信就是六七天时间。我一看,是让我去复试。到榆林后,是榆林县的领导在复试。当时领导不看,是让我们录音。所有人都在排队,整个钟楼巷都站满了。都是年轻人,大学毕业的,高中毕业的……我一去,人家就认得我,“哎,你来了,你同学呢?”
“不好意思,就是我。不是我同学,是我。”
“我们那阵儿就觉得是你,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老实!不说实话。”
我把前因后果,清涧怎么考的,有什么心理负担都给他说了。人家也很理解,“哦,是这样。你就不要跟他们在这儿排队录音了。”就叫了杨焕荣(现在退休了)拿了一台录音机,提了一壶水,开了一间编辑室,说,“你就到这个房子录,你什么时候录好了,什么时候把带子交给我。”中午到那儿,下午快下班才录好交了带子。他们准备的一篇稿子,我自己准备的一篇稿子。录音完了还有笔试,交卷后人家让回家等消息。
我二爸当时在行署,我来考试没告诉他们,当天下午我去他家才说我来考播音员。我二妈说,“你念念,让二妈听听,我就不信你的普通话比你毛哥的普通话还好。”我一念,行署大院好多人跑二妈家来了,“哎,霍队长你们家放电视,我们来看看。”结果不是,是我在那儿读报纸。
大概是7月份,又来了一封信,“霍宝林同志,你已经被榆林县广播站录取为播音员。请你见信后速来榆林报到。”这样我就成为榆林县广播电台第一批合同制员工之一。
“惹事”的负面报道
1985年8月14号我到榆林广播台报到,给我分了宿舍,就在钟楼上。当时我觉得这个播音员职业很神圣,却对编辑和记者的意识很淡薄。编辑编好的稿子,我认为对,我就照着播,我认为不对,我就给改了。我不知道,谁也没教给我,其实这个在新闻界是一个“大忌”。编辑编好以后,不可以改的。除非你自己看出来非常明显的错误,哪个字错了,你告诉编辑,编辑改过来你再播。而不是你自己直接改了播。
1987年有一次机关作风整顿,我们有一个记者,在榆林行署、榆林地委、榆林县委、县政府大院儿里蹲守了半个多月,写了一篇报道,有三页多,应该有一千多字。迟到的、早退的、上班期间办公室没有人的,他都写了。这个记者可能比较年轻,甚至在报道里点了谁谁谁迟到、早退,几点来的,几点走的……我们编辑大部分都划掉了。用红毛笔划掉的,但红色下面还能看得到原稿。我一看,机关作风整顿,大会小会上强调,这么好的稿子改成这样了,编辑不对。我就按原稿播了,全部播了。播出之后,影响特别大,榆林地委马上就开会整顿,把报道里提到的人给处理了。当时的处理不是口头批评、做个检查那么简单,就是真处理了。这下他们受不了了。我们局里就开会,领导问,“谁把这个稿子播出去的?”
“霍宝林播出去的。”
“为什么播出去?”领导开始批评我。我还据理力争,“我们记者那么辛苦,多长时间写的这篇稿子,你把稿子改成那么点。咱们地委领导一直在强调作风整顿,大会小会那么开,我也参加会议了。我们作为舆论监督,人家写了这个稿子,就应该如实汇报,为什么不播?”
“哎,你还强词夺理!这不能改!”
“你就不能删!”
领导一气之下就让我做检查。我不做。开两次会批评我。批评我,我不干了!我就辞职了。我就把合同和辞职报告交到办公室那里,不干了。把办公室的人气得,“你这后生,太不知高低了!”
在这之前,我接到丁涛老师的电话,“我办了个培训班,大专班,想让你来培训。”1985年年底,为了提高各地县播音员的文化水平,丁涛在西北大学办了一个播音员培训班,招收全省各县播音员。但我是87年才知道的。单位不想让我去,怕我跳槽。最后我还是去培训了。去了以后,单位也没办法,回来以后还给我报销了费用。那会儿单位对我挺好的,每星期回一次清涧,来回车费全报。后来我总结,还是我有些伤了领导的心了。因为太年轻,就那个事情上让领导下不来台,就辞了。再说丁老师跟我说,省台想要人,他那会儿是省台的播出部主任,专门管播音这一块儿。丁涛老师上课时就觉得我这个嗓音条件啊,播音水平都挺好的,想培养我,让我破格到省台去学习。所以我递辞职信也不是很盲目的。

播音要带点“京味儿”
我辞职后,去省台实习。省台招人,给省劳动厅打报告,要劳动厅批,这个周期比较长。半年以后,丁老师去世了,就把我搁在一边了。后来是海茵老师跟我说,“小伙子,你在我们这儿挣不上工资,没有前途。丁涛老师去世了,我们这儿暂时也没有人负责。你跟你的同学联系一下,看可不可以到哪个市台去干一干。市上手续比较简单,要人也多,像你这样的一定没问题。”
我就跟同学们联系,我们西大一起学习的同学,都是各地县的播音员。宝鸡、咸阳的同学都说要人。我都去试播了一下,最后决定在宝鸡干。宝鸡有我两个同学,关系都特别好。我在宝鸡干了一年。
当年西大学习时教我们语音学的吴天慧教授,曾经是中国四大语音学专家之一。他是从江南到西北大学任教的老教授。我对老师恭恭敬敬,又很勤快,学习刻苦,业务也比较突出。老师们对我都挺好,知道我经济上比较困难,所以常叫我到家里吃饭。吃饭的时候看电视,吴老师就给我讲,每个播音员哪里是优点,哪里是缺点。这个字音是怎么读,那个句子是怎么断。我就问他,“咱们陕西台播音员和中央台播音员,那个语音一听就差别很大,为什么呢?”
吴老师说,“陕西的语言环境就是这样。”
我说,“那咱们能改吗?”
他说,“改不了,没法改。除非你到北京去,你在北京那个语言环境下面,你听北京那个小孩的发音,你跟他们学上一点儿就够了。我们的普通话,不能光照着拼音去发音,你要带点京味儿就好听了。”
我说,哦,原来如此。从此我就有了到北京去的念头。
到宝鸡一年后,我得了宝鸡优秀播音员二等奖。我觉得自己离真正的优秀还差的很远,宝鸡也不是久留之地,干脆就再去学习巩固。宝鸡台是大台,有个同事叫谢香,她说“小伙儿你想去北京?我有个同学从西藏台调到北广当老师了。叫张秀清,你去找他,我给你推荐。让他给你安排下食宿。”因为家里不支持我,所以经济上一直比较困难。到北京后,张秀清就给我安排到他的宿舍去住。她也带课。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姚喜双,是国家语委主任,今年退休的。张颂教授给我们上的播音主持课。
我去北京时,是1989年。我妈给了我400块钱,我爸一分钱没给。路费就花了大几十块钱,还剩几百块,压根没敢动。吃饭就去老师家里蹭,给人家收拾屋子、擦擦桌子什么的,花费很少。后来我就到北广附近,定福庄,一个农家院里头,和我的两个内蒙同学一起租了间房子。就为了跟院子里的小孩儿接触,在那儿呆了半个月,房租大概100左右。400块钱快花完了,也到年底了,就回了家。本来第二年1990年,开春还得继续上学,上完给文凭。结果我学费没交,当时学费要一千多两千块钱,我拿不出钱,也拿不到文凭。之前在西北大学念那个专科班也没交学费,没有拿到文凭。
90年开春,我准备到深圳去,知道那里在开发。我先到四川内江,那里也有个西大的同学,到他那儿待了几天。他说,就到他们这儿干。我说不行,我想到深圳去。准备离开内江的时候,给家里打电话,实在没钱了。我把我带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。我说能不能给我点钱。我妈说,“要钱你只能回来。不回来不行,比我年轻的都抱孙子了,你赶紧回来。你不要找工作了,我把你养活上。再不允许你出去了。”我当时想,自己出去确实很苦,再一个,家里也就我这一个独苗,我有四个妹妹。我出去后,大人都很担心。出去了万一哪天死了,这个谁也说不来,对不起生我一回的父母。算了,就当个孝子吧。就回来了。
回来以后,家里就赶紧张罗着介绍对象,没工作对象不好找。我就说,“不就找个工作吗,我再找就行了。”我妈说,“就在咱们这儿,不要远了啊!”
我去榆林台找工作,找到杨海燕,那会儿是台长。我说我想回来,哪里要播音员?
她说,“好么,只要你想回来。榆林电台现在人已经满了,米脂、靖边、佳县、神木这四个县,你挑。你先去看看,我给这几个县都打个招呼,你想到哪个县就哪个县。”当天晚上我到了神木。我待了一天,觉得那个小楼环境不好,离家也远,所以第二天就走了。我又到地区广播局,杨海燕说,“要不你就到米脂,那儿是清水衙门,人们文化素质也高。又是文化县,离你家也不远。”
我到米脂后,米脂广播局给我把宾馆的房间都登好了。接待我的是编辑郭思焕,还有高局长(高德怀)。问我想来的话,有什么条件?我说条件很简单,把我的工龄延续上就可以了,我从1985年开始工作的。局长说,那个好办。完了我就上班了,在广播台。那会儿没有电视台,米脂电视台是1993年开始筹建的。
广播电视的市场化应当是服务的市场化
近些年国家对广播电视行业进行改革,说是事业单位,企业管理。按照改革方案的话,经营费用是财政负责一部分,剩下一部分自负盈亏。先是财政给三分之二,然后是二分之一,然后是三分之一,最后彻底市场化。等于是把党的喉舌,政府的宣传这一块推向市场了。米脂广播电视台的市场化改革一直没有实行,为啥,因为真实行了这帮人都得饿死。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拿着全额工资。近几年广电局改成了广电中心,这才正式与文化局合并。之前说是合并了,人事、财务、业务都是独立的。每年的考核,也成了文化局派人过来考核我们,以前是组织部来考核。
90年代,广电部门走穴很厉害,再加上广告的爆发,各种各样的广告,不讲究质量,只要给钱,什么都做。从那时开始,人们没有底线了。中华民族几千年,不仅有底线,还是有文明的。现在不仅没有文明了,连底线都没了。为什么?就是从这段时间市场化后开始的。不是还有人鼓吹军队独立化吗?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包括这个宣传文化阵地,意识形态领域这根弦,必须要党管。
米脂广电局曾经把广告部给承包出去,但是赔了,亏本了,再没人做了。差额以后,存在个创收的问题。怎样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?什么东西才能获取最大利益?暴利行业。正路行业就不存在暴利。所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,是不可取的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《如果我是台长》。我不会靠广告创收,我靠服务创收。现在社会对广播电视的需求是非常大的,人人都是摄影师,但是不是人人都会制作、都有平台去发表。我们服务于他,提供平台。你有好的作品到我这里来播放,我可以给你提供录音棚,提供演播室;你有才艺可以到这里来展示。这样节目源也充实了,创收也创收了。市场化,它实际是服务的市场化。向市场服务,不要高高在上。我在服务党,服务正确导向的同时,面向市场,提高服务质量,这个是正确的。现在不是这样做的,只是广告创收。

霍宝林近照
发掘地方文化和红色资源
我本身是个有故事的人,又对故事很感兴趣。故事必须讲,故事不能看,看着没啥意思。我以前想搞个台,但政策不允许。现在自媒体发达,我想建一个网站,我讲讲故事,这个不违反咱们的政策。
我现在搞专题片拍摄,也是市场需求。人家需要,我去做了,我是在服务。我一年赚几十万没问题。我全凭业余做专题片才敢买房子,买车,孩子们每年各种培训费,每年参加各种比赛,出去旅游……我做的专题片,在行业里评得比较好的有《铁水打花》《李自成传说》,纪录片有《闯王桑梓行》,获得省上广播电影电视二等奖。米脂的非遗项目专题片,都是我做的。项目申请由文化馆负责,我与他们合作。因为申请项目必须要有片子,音像资料比较直观。像铁水打花、李自成传说故事、貂蝉传说故事、米脂唢呐也是省级非遗项目。今年省级评审的是非遗传承人,一个是唢呐的,一个是李自成传说故事,再一个就是铁水打花的传承人。我们走访很多人,从里边选出比较有代表性的,做成片子。
2016年,我做过一个广播剧。当时,国防部要求全国各军警机关,以改革强军为主题,发掘一些宣传正能量的作品。米脂县武装部部长就找到我,说想做个微电影,但时间比较紧,就一个星期左右,问我能行不。
我说做不出来,要找本子,还要拍摄,还有后期。
“那你做什么比较拿手?”
“我做广播拿手。做成广播剧行不?”
“那也行。”文件上节目类别里有一项广播剧。他也是个陕北迷,“陕北这么多红色资源,我们就在这方面挖掘。耳熟能详的或者鲜为人知的,都可以。都说米脂婆姨,漂亮、贤惠,咱们不能从红色方面挖掘一点?”
我到网上查,找到一篇口述的稿子,采访的是曾参加沙家店战役的一个老大娘,叫郭兰花。根据这个稿件,我简单地编了一个广播剧。我通宵没睡,第二天一早打印了几份稿子,发给几个演员。部长也是演员。录音就在文化馆的二楼。中午十二点,录完了。我后期制作的时候一听,不行,根本不行。演员不行,尤其是演老年兰花的演员。文化馆馆长史飞说,有一个演员,曾经在米脂剧团扮演老生,现在年纪大了退了,在榆林住。不知道你请动请不动,电话给你,你给他打。我打过去,说,我是霍宝林。
“哦,霍宝林,我知道你。”
“我们排一个广播剧,要一个老年兰花,非你莫属,你来演行不?”
“好好好,我非常愿意,你要是早说,我刚从米脂上榆林。那我赶两点下来怎么样?”当时十二点左右。
我说,“行,太谢谢你了,你几点来算几点。”人家两点准时到。不讲工钱,没工资。最后我个人掏钱,给每个人二百块钱。所有演员都是我现场导演,现场教,教一句录一句。录完我又做了后期,因为要的急,我觉得做得比较粗糙。给大家一听,都愣住了,诶,原来这么好。这个剧名字叫《沙家店战役中的米脂婆姨》,策划的名字写的是武装部长,编剧写的是一个武装部干事,因为这个是全军内部评奖,外部人不可以评。送到陕西省军区,获得陕西省一等奖,推送到北京,评了个全国二等奖。
(2018年8月3日采访录音,8月5日整理完毕)
霍宝林口述 申元元整理